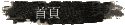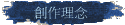|
|
|
|
|
|
|
現階段之繪畫創作觀 一傳統之陶冶與學習歷程 運筆與用墨 中國畫之學習與創作相較於西洋畫,實有大相逕庭之處。學者從入門伊始,便需對運筆、用墨之基本功夫做種種之研究與持續之練習。 毛筆之製作過程甚為特殊繁複,其毫端甚為柔軟,不議長喔。書寫者卻須以此顯現力道與富於變化美之線條,並求其剛柔必濟,方圓相輔;優雅流暢而不偏滑,含蓄內斂而不停滯。運筆之中,依其壓力之強弱及速度之緩急,而形成抑、揚、頓、挫、情韻靈動之線質美。因此,初學國畫者,若冀其來日有成,勢須在用筆、用墨之上勤下苦功,契而不捨,做長期之鑽研與訓練,此乃一窺國畫堂奧之礎石與近接。捨此之外,別無終南捷徑。 而用墨與用筆二者之間,實有密不可分之關聯。毛筆固可依其中、側、逆鋒或筆鋒、筆腹之捽、擢、掃、擦‧‧‧諸技法靈活運用,任意揮霍。然所顯現之線條,無論昰乾、昰濕;無論是飛白,或是豐盈飽滿;也無論千種濃淡或萬種氲氤,若非善於用墨之人,絕不能竟其全功。 筆墨之間,譬如車之兩輪,譬如鳥之雙翼,須天衣無縫之配合,相輔相成,方能盡情傳達宇宙間森羅萬象,方能抒發心靈中無限之風情。否則太重筆而輕墨,或只言墨而忘筆,則如鳥之折翼,輪之孤走,偏頗歪斜,欲求意境之高,戞戞乎其難矣。 進一步言之,筆墨之間尚有大學問在。在用墨上,古人一直強調「墨分五彩」,正說明墨與水份巧妙融合,所產生之墨韻變化。誠如近代畫家李可染在其畫論中所稱:「筆墨昰形成中國畫藝術特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畫家有了筆墨功夫,筆墨與物象渾然一體,筆墨腴潤而蒼勁;乾筆不枯,濕筆不滑;重墨不濁,淡墨不薄;層層遞加,墨越重而畫越亮;畫不著色而墨分五彩。筆情墨趣,光華照人。」李氏之論,充分闡明用筆、用墨之要領及二者在中國畫中之重要性,初學者不可不知。
傳統與臨摹之思考 相較於筆墨之基本功,余以為傳統之繼承及臨摹有其不可輕忽之處。先言臨摹。清鄒一桂在小山畫譜中,曾提及「臨摹即六法中之傳模,但須得古人用意處乃為不誤,否則與熟童印本何異夫,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固矣。賢人之言庸人述之而謬矣。一摹再摹,瘦者漸肥,曲者已直,摹至數十遍全非本來面目,此皆不求生理於畫法未明之故也,能脫手落稿杅軸予懷者方許臨摹,臨摹豈易言哉。」鄒氏之語最得我心,彼雖極言臨摹之不易,甚或以嚴詞厲色撻伐不當之臨摹,但亦正以叮嚀學者臨摹之重要性,與危險處,容不得一絲輕忽。尤其不可不深入其「用意處」,否則難免落至臨摹愈多而肥瘦曲直愈亂;臨摹愈多而畫意畫境愈卑下之窘困境地。「能脫手落稿杅軸予懷者,方許臨摹」之言,的確值得學者反覆咀嚼,思之再三。 次言如何看待傳統。近代畫家李可染在其畫論上之言最當思索。「藝術家是藝術規律的探索者,我國自古以來有那麼多才華洋溢的藝術家,歷經艱辛,探索了幾千年累積了豐富的藝術經驗,構成了中國畫的優秀傳統,誰要昰丟掉傳統,誰就是最大的傻瓜。」誠然,能師古然後可以創新;能繼往然後可以開來;能入於傳統然後可以突破傳統。李氏之語對一味拒斥傳統,不計代價追求現代之人,實不啻當頭棒喝,其醍醐灌頂之醒世作用,實能深獲我心。眾多追逐現代,營求新潮之人,瞻前之時,是否亦應有後顧之念? 綜上所述,可知古今畫者對傳統筆墨運用之學習與臨摹何等看重,後學之人決不可怠慢輕忽,甚至加以鄙薄拋卻,否則必與所追求之畫境,背道而馳,漸行漸遠矣。
學習歷程之追憶 個人自幼便喜塗抹作畫,但與水墨結不解之緣,且持續不懈至今者,仍須回溯一九六五年進入嘉義師範就讀之始。嘉師求學生涯三年之中,余以飢渴之心,飽 傳統筆墨之精華─清四王蒼茫身秀之風致、元王蒙高古鬱茂之風華、唐寅清雋之風神、文徵明溫潤雅致之風韻,皆為個人長期沉潛臨摹之典範。 在此時期,余頗能從臨摹中領悟先賢繪畫殿堂之華美富麗,感受古人創作天地之遼敻無垠,驚嘆前人登峰造極之墨韻筆意,而大興「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雖不能至,心嚮往之」之心。發願在水墨之沃野禾田, 力耕耘,俾其開花結果追古人畫境唐奧於萬一。宋文信國公正氣歌所云「典型在夙昔,古道照顏色」恰為此時期之心境寫照與個人繪畫進程之景況。然以普通師範之程度,並不足以滿足個人對正規美術學院之嚮往。因此,任小學教職服務三年期滿後,即先後考進國立藝專及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深造進修,正式接受較高層美術教育之洗禮與考驗。 藝專美術科系有極堅強之師資陣容。藝專三年,在諸名師之薰陶下,無論現代繪畫理念之汲取,或傳統筆墨之研習,皆奠下良好堅實之根基。在美學、美術史、藝術概論…諸學科理論之配合啟迪下,我如禾苗幼樹,飽 甘霖澆灌,飽享春風吹拂,真可謂茅塞皆開,樂在其中。藝專歲月豐富堅實,對個人之繪畫生涯規劃,有決定性之影響。 文大二年,則又是令一段豐富之旅。文大乃今日嶺南畫派教學之搖籃重鎮。該派對光影、色彩、氣氛之處理與掌握,有其獨到之處,其韻味十足,涉筆成趣之妙法,令人有藝海空闊任我航行,畫地無邊足資翱翔之歡悅。 然而,藝術之海何其遼敻,繪畫之江河何其深邃,愈深就愈覺其「百官之富,宮室之美」之魅力無限而目不暇給,愈鑽研愈增其「瞻之在前,忽焉在後」之崇仰情懷而嘆為觀止。此種仰慕深羨之心,時時在胸中澎湃翻騰,成為激勵無人揮別舊家邦,尋找另一新樂土之原動力,亦促成後東瀛為時三年之因緣契合。直至學成歸國,求學之過程方暫且畫下句點。
二、徜徉寫生與創作之間
寫生理念之探討 初學國畫者,常以臨摹為其起步。前已言及臨摹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。其目的在於未窺堂奧之初,藉畫稿、畫冊、古畫之方便,窺見古人自然樸拙、剛柔並濟之用筆;揣摩古人濃淡乾濕,千種墨韻之用墨方法,以精進一己繪畫之技巧。 然臨摹畢竟有其不可突破之局線性,蓋因畫稿有時而盡,圖片有時而窮,題材之擇取增減,時時受囿受限,唯有「大自然」方能滿足一切需求,蘊含無限寶藏,永遠取之不盡,用之不竭。因此,個人在勤練筆墨功夫,勤學種種繪畫技巧之外,便以寫生為創作之進階,藉大自然景致之無盡變化,豐富作品之內容,避免落入師承及臨古之形式窠臼,並提昇日後創作之原動能力。此項努力,至於今已逾三十載。寫生之地,遠則歐美大陸,近則寶島各地,山嶺鄉野,湖畔溪邊,無遠不至,幸能日有所得,月有所進,而自感無負平生。 寫生之說,起自唐貞觀九年彥悰所寫「後畫錄」評述殷王府法曹王知慎所云:「受業閻家,寫生殆庶。用筆爽利,風采不凡。」此為「寫生」二字影響中國繪畫之重要記載。 其實,無論往古推溯,抑往後稽考,畫壇巨擘方家論及寫生在創作上之重要地位者,彼彼皆昰。鮑少游在其「畫論集」中曾云:「考我畫史,唐宋畫法,上承魏晉六朝,下啟元明兩代,新範競舊,後傑並起。且堂皇深邃,法度森嚴,尤重寫生,並重神趣以為創作,故能合乎正常而致於精妙,巨製尤夥,論者稱之為璀璨光華,卓越千古,誠非過譽。」言及唐宋畫作之精妙,特重寫生。 南齊謝赫「古畫品錄」所指六法之「應物象形」意指寫生。晉顧愷之言「以形寫神」。張 謂「外師造化,中得心源。」非僅道及寫生之內涵,更將寫生與創作等同看待。美術史家俞劍華在「中國繪畫史」裡,對何謂師造化做一註解:「師造化寫生也,得心源創作也,作者人格之具體表現也。」心師造化,意指以造化為師。造化,原是指稱自然界,後來泛指一切客觀事物,師造化成為我國古今畫家身體力行之創作原則,其重要性不可言喻。 近代畫家李可染亦在其畫論中,格外強調寫生之重要性。彼以為「寫生昰畫家奔向生活,認識生活,豐富生活感受,累積創作經驗,吸收創作源泉的重要一環。」凡此種種,無一非先人對寫生之看重,寫生之於繪畫創作其重要性與影響力,由此可知矣! 對寫生之重視,中外畫家皆然,十九世紀畫家布登〈Bondin〉即曾指出:「再就地寫生所畫出來的每一件事物,都有一種力量,一種活潑的筆觸,這是畫室裡無法再創出來的。」此為布登經驗之談,的確不容忽視。德國哲人康德亦云:「藝術以模仿自然,得其全神為極則。」更將模仿自然之寫生原則一語道盡,令人佩服。 個人以為,寫生至宋代畫壇有一相當革命性之變革,蓋宋代融合理學、詩學與禪學三種思想,三者相互激盪,對豐碩寫生內涵與境界之提昇,有極大之貢獻。 彼時特種寫生,且其寫生有往昔所少見之特色。此種寫生特色為何?簡易言之,即精神超乎形式,時空之轉換超乎實景描摹,但又不失自然合理性之寫生。如以范寬「谿山行旅圖」為例。前景之闊葉樹,中景之針葉林,遠至高海拔之灌木密林,同時出現於畫面之中。此種佈局法,既兼有超脫凡塵之情境,又顧及自然之合理性,可謂宋畫寫生之一大特色。 若論及寫生之理念,郭熙之見識頗足稱道。彼在「林泉高致」中強調:「針山水之煙嵐,四時不同,春山 冶而如笑;夏山蒼翠而如滴;秋山明鏡而如妝;冬山滲淡而如睡,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。山朝看如此,暮看又如此,陰晴看又如此,此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。」 在此段話中,郭熙對寫生之認知,非僅注意春夏秋冬四時之不同,抑且洞察晨昏午夜,朝暮陰晴之時空差異性。彼能有這般卓然識見,無怪乎能盡言寫生之妙諦,且為後世學者之所步趨追隨矣! 元明以降,文人畫風行,有以繪畫乃逸筆草草,不求形式之主張,然亦有部份具前瞻性之畫家竭力實踐創作。在「中國畫論類編」中,元黃公望有「皮袋中置描筆,或於好景處,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之,分外有發生之意。」之載記。「苦瓜和尚畫語錄」中云及石濤「搜盡奇峰打草稿」,主張「信手一揮,山水人物,鳥獸草木,池榭樓台,取形用勢,寫生揣意,運情摹景,顯露隱含,人不見其畫之成,畫不違其心之用。」對寫生,真可謂情有獨鍾矣。除此而外,沈周、八大山人亦有諸多寫生畫蹟、冊頁傳世。 凡此種種,不一而足,而尤足稱道者,在歷代宗師碩彥,非惟高唱寫生之不可缺,其自身且亦為寫生創作之有力實踐者。由昰觀之,彼對後世繪事之影響,當非僅推波助瀾之小功而已。 深受先賢創作精神與窮理致知態度之感召,多年來,個人無日不競競業業,謹守此種精神態度,並以之為寫生創作之最佳圭 。個人在近年舉辦之個展中,寫生之作已成主軸,且自認已稍具心得。前人所謂「外師造化,中得心源」之妙境,乃我之所願,而我亦以此作為終身 力之目標。
移動之透視觀 在運用技巧方面,中國畫之寫生甚少運用西洋繪畫之固定透視,而採以不定點透視法處理,此即所謂移動之透視觀,先將對方做不同角度之徹底觀察認知,以求掌握對象之全體。對國畫而言亦惟有採用此方法可掌握寫生之精隨,以臻前人所謂「格體精微」要求。欲達「格體精微」之最高境界,首要條件乃在「格物窮理」。格物窮理之意,即禮記大學篇所云:「欲誠其意者,先致其知。致之在格物。物格而後知至,知至而後意誠。」之謂也。此種將客觀之認知,逐漸轉為主觀造意之過程,即昰繪畫者從觀察、寫生以至完成創作之完整過程。以移動之透視觀寫生,大抵須經此歷程,學者不可不知。 昔郭熙稱「山形步步移,山形面面看」,蘇試題西林壁謂「橫看成嶺側成峰,遠近高低各不同」,二者皆中國畫著重面面觀察,重新立意,且看且畫之移動透視觀。運用此法則時間之連續性及空間之延續性,皆可在畫面之中獲得完整之呈現與突顯。此又與國人天人合一之心性修為有關。中國人看山,可以客主相合,可以情景交融,甚且可以達到物我兩忘之境界。在山形步步移,山勢面面觀之中,令咫呎之素展現千里秀麗江山,以篇幅表達無限寬闊景緻。經由此法可以創造「十樹成林,十屋成村」之效果,經由此法可以成就張大千先生氣勢磅礡,欇人心目之「長江萬里圖」。移動透視觀之為用大矣哉! 寫生之法,大致可以直接寫生及間接寫生二法涵蓋之.。前者重在面對客體,從諸多不同角度做深入觀察,以為直接之描繪;後者則憑觀察後之心得,透過作者之獨特創作意念,以表現對象之精神,此乃間接寫生之重點所在。 欲掌握寫生之要領,則以黃公望所謂「每見老樹奇石,即囊筆就貌其狀」之精神態度為不二法門。若欲完美間接寫生之創作,須能做到「萬物寓於胸中」,甚至達到「取物不惑」之境地。如此,方足以言寫生。
創作之我見 「創作」乃畫家之生命,畫家之靈魂,缺乏創作,便無藝術可言,此無千古不移之定律,亦當為每一畫者所宜拳拳服膺者也。 於是,學習古人與自我創作之間,如何相佐相輔而不相阻相礙,頓然成為一大問題、大疑惑。對於此種困境,明石濤上人有一番告誡之語。彼五十二歲時,曾於畫上題跋之中言及:「古人未立法之先,不知古人法何法,古人立法之後,便不容今人出古法,千百年遂使今人不能出頭地之冤哉。」如何看待古法,此語實值得無人深思。 白石老人曾有劇力萬鈞之語:「學我者生,似我者死。」此語極深沉,意在告誡後學不可食古不化,貴能推陳出新。不然,將永遠背負傳統窠臼之包袱,而無法另闢蹊徑,樹立獨特畫風。 白石老人之理念深獲我心,影響至大。憶及藝專、文大到筑波大學,都屬於正規之學院派美術教育,學校有一套完整之課程安排,教授有一套教導學生精進之固定方式,此法,學生雖然進步神速,但不易脫離老師之畫風。老師經驗豐富,見聞又廣,均已樹立獨特風貌,但白石老人「學我者生,似我者死」之警訊,令個人和曾涔涔而下而深有所悟。因此,多年來,以師承所奠定之創作基礎,不斷尋求新風格之突破與建立。如今,已稍有領會,當再求進一步之自我超越,以不負諸師引導教誨之辛勞與功勳。
創作之方法與過程 個人以為創作之法可分為:用意之創作〈即理性之創作〉與率意之創作〈即感性之創作〉。用意之創作,重點在於創作之過程,經過精心之準備與萬全之計畫,以及完成後之檢討與修正。其順序約可歸納為: (一力意: 創作者欲表現何者內容?何種意境?須先「胸有成竹」。因立意乃作畫之肇始,畫作之靈魂,立意不高,便無憾人心弦之作。面對畫紙絹素,須先思索我將表達何種意境?傳遞何種訊息?昰山川之壯麗?昰人情之深微抑或生物之意態?昰修竹之清風亮節?昰蕙蘭之風致翩翩?抑或寒林之荒野孤寂?……都得立意在先,方能構圖著筆。簡言之,立意乃創作態度嚴肅認真之表現。 (二)尺寸形式: 紙之橫直、大小,將直接影響一幅畫之立意佈局,大畫有其大磅礡之勢,而小品亦有其雅趣雋永之情,取捨之間,皆視其立意而決定之。 (三)素材選擇: 作畫之素材攸關創作效果甚巨,筆鋒有剛柔、長短之分,墨有松煙、油煙之別,而紙張之種類繁多,諸如紙之厚薄、表面之加工……等,在在與作畫效果息息相關,不可不重視。 (四)資料收集與應用: 作畫之前,資料之收集越多,則愈能充實創作之內容,豐富創作之作品。如石濤老人所稱「蒐集奇峰打草稿」便昰隨時收集速寫資料之最佳途徑。另圖片、照片或文字等說明,均須盡量收集,以利創作之用。 (五)構圖: 在原寸之等比例縮小紙上做構圖練習,務求畫面之賓主、均衡、疏密、虛實、藏露、呼應……等構圖要點,面面俱到,以求完美。 (六)製作: 經過縮小圖之謹慎安排,力求完美再行原寸作畫。 (七)檢討修正: 當作品完成時,須作檢討改正,若有不妥處,或無法達立意之要求,則再行修改,反覆斟酌,直至滿意為止。 (八)再製作: 當完成品有瑕疵,經過反覆修正後再行製作,以合原先立意之要求而臻盡善盡美之境。 製作大幅作品費時甚長,動輒數日方可完成,今日之思緒與昨日之想法未必相同,甚至可能相左。如此極易造成意念之不連貫,影響作品之一致性,嚴重者且有半途而廢之憾。因此,若能依上列順序做妥善安排,採用意之創作,則不僅上述所言之缺失可迎刃而解,即孕育創作之思緒得以多方培育,而激發創作靈感之泉源,亦可 流動矣。 至於率意之創作,重在「無心」與「自然」,達到所謂「信筆拈來,一揮而就」之境界。然而,理想之率意創作須以用意之創作為基礎,缺乏用意創作之訓練,必難以達成率意創作所欲達成之目標。誠如李可染先生所云:「經意之極,若不經意」。 因此,先「用心」再「放心」之道理,卻有其意義在。 在個人作畫經驗中,率意創作常用於小品畫中行之。面對畫紙,立意已定,則信筆拈來,一揮而就。如以菖莆為主題之「供養」、以「佛」字為背景之「清靜心」等作品,均不經太多考慮,不作太嚴謹佈局下所隨意完成之作,作畫時間雖短,卻頗能得心應手充分表達畫意,此即以率意之心完成作品之謂也。
三、 艷彩風格之孕育與形成
色彩新觀念之啟迪 民國初年,西風東漸,中國傳統繪畫承受極大之衝擊。改革之思潮迅速滋長蔓延,守舊之力量日漸受到挑戰與質疑。 尤其,一九五七年「五月畫會」及「東方畫會」之相繼成立,更帶來巨大之變革。雖然,畫會成員均以研究西洋繪畫為主,但他們所散播之嶄新理念,在畫壇掀起種種波瀾。連帶亦造成台灣新生代畫者對表現技法及素材之求新求變。個人躬逢其盛,也曾為此而重新調整創作之思維。 個人在文化大學美術系求學時,開始接觸重視光影、色彩之嶺南派畫風,此時正為研究色彩注重色彩之一大契機。 嶺南畫派之興起,不過二百多年,由居廉居巢兄弟始,經高劍父、高其峰……諸大家進一步研究與發揚。自傳統繪畫之中萃取其活潑、生動且富乾、濕、濃、淡變化之筆趣,並融合西洋畫中光影、色彩之效果,使水墨與色彩之融合臻至自然之妙境。因此,文大期間,個人沉醉於嶺南畫風之學習與鑽研,此後對個人艷彩風格之建立,有甚大之裨益。 然美中不足者為:嶺南派注重色彩之畫風,所給予個人之啟示-對色彩研究與開發。在缺少色彩變化之台灣環境,終究有難以突破與發揮之憾恨。於是有改意環境之強烈意念,赴東瀛求學之計畫於焉而產生。
東瀛三年之體驗 一九八三年春,美夢成真,入日本筑波大學研究所,以彌補昔日所學之不足,並期待改易新環境之後,能在新環境之刺激中,力求創作瓶頸之新突破。 東瀛大學四季分明,色彩常隨四時之遞嬗,而有新綠、濃蔭、霜紅、飛雪之變換,呈現多姿多彩之艷麗與嬌美,處處是盎然無比之生機,時時有繽紛多變之驚喜。對於長年深處亞熱帶地區之個人而言,乃一種勾魂攝魄之震撼,更有一份欣喜若狂之歡躍。於是,大膽敷施艷彩之心,油然而生,奠定日後畫風丕變之因緣。 東瀛大地中,除春之桃紅柳綠、夏之翠碧濃蔭、冬之冰雪寒霜令人賞心悅目之外,秋之富於色彩,最令人感動震攝-落葉松林遍染金黃,山間湖畔楓紅似火,雲淡風輕,落葉片片,徜徉期間,詩情入夢。不由不憶起石濤老人詩中所云:「秋風吹下紅雨來」之畫境。秋林放歌,心馳意蕩,不知何時「日光之秋」「紅雨」「秋霜」之景,已勾勒於胸臆。因之留日期間所有畫作大多蘊含強烈之色彩與濃郁之扶桑風情。 較之在台灣故鄉所學,以清淡素雅之清四王為臨摹對象,不免有只求淡雅而不敢敷施艷彩之傾向。如今則恍然開悟-其實色彩在中國畫史上有其甚久之淵源,只因時易境遷,受文人畫追求淡雅、注重墨韻畫風之影響,方始色彩隨之減損,而盛行以淺絳代替重色而已。 從晉顧愷之「雲台山記」及其他紀錄上可知:我國古代繪畫原多色彩濃麗、五彩繽紛之青綠山水。「雲台山記」上云:「天及水色,畫用空青…」可想見其時以青色敷染碧空,使畫面呈現鮮豔奪目之情景。此和近代繪畫天空留白之畫法大異其趣矣。再證之故宮所藏唐代「明皇幸蜀圖」,其以石青石綠之設色,本已色澤斑斕,光鮮動人,又以泥金粉勾勒其邊,益增金碧輝煌之唐畫風采。色彩在早期之深受青睞,由此可見一般。毋怪乎它要成為謝赫「六法論」之賞畫標準之一。 李霖燦先生在中國畫史研究論集曾提及「不論一幅畫為大青綠或小青綠,只要它不違背諧和雅靜這項中國正統的原則,不怕它設色濃厚,只要不艷俗逼人,能給人一種華麗而不庸俗的感覺,或翠羽明璫莊靜照人,或一片斑斕如古錦 絲 絲;再不然是淡彩淺絳,給人一另一種詩意盎然的感覺,或淡雅如空谷幽蘭,或古雅如山中高士,那麼,這些畫的設色就是成功的。反之,那就是壞的設色了。」足見無論濃艷或淡雅,若能設色完美便稱佳作。換言之,設色完美與否,方昰成敗之關鍵。既然如此,則如何將艷彩用之水墨中並使之安定自然,形成艷而清雅,艷而不俗之境界與風格,遂成為個人日夜思索及追求之目標 。 再者,個人以為傳統文人畫,雖淡雅高古,但刻意輕忽色彩。畫者對藝術創作與在此時大倡藝術創新之呼聲中,實為自我囿限,自我束縛之舉動。因此,色彩成為一項可重新開拓之一大領域,乃屬理所當然之事。試想,大自然之中,四季之艷,百花之紅,新芽之翠綠,落葉松之金黃…,何者不繽紛?何者不鮮明?何者不艷麗多彩?於是,乃嘗試在畫中減少 擦之線條,代之以重墨及多層次之烘染,時在半乾之墨中添加筆觸,時在全乾後之墨中增益線條,一則以安定濃艷色彩之輕浮性,顯現自然墨韻之變化與古樸蒼潤之美;再則可達成艷而清雅,艷而不俗之理想境界。此種創新與嘗試,在日期間,幸深受日本畫壇友人之重視與讚賞。
艷彩系列之創作與延伸 一九八六年自日返國起至一九九一年之間,亦持續從事此種艷彩之創作與開發。尤其潛心將扶桑三年積累之經驗與創思,色彩與水墨融合研究之心得,予以消化吐哺,區分黃、紅、綠、灰、粉紅等五種系列。分別對色彩與水墨之容合做嶄新之嘗試與創作。 創作之成果,包含一九八七年應歷史博物館之邀,假國家畫廊舉行「自然的禮讚-四季之美」專題個展,此乃個人對艷彩研究心得之首次展示。一九八九、一九九O年,又分別推出大地歌吟系列「繽紛之美」及「自然的艷彩」之主題個展,此又屬艷彩系列作品之另一次揮灑,亦為艷彩與水墨融合之另一新詮釋。此類可艷麗、可清雅之表現方式,幸獲年輕畫者之喜好,激發其研究之興趣,此對水墨畫推向現代化之過程中,實扮演一推波助瀾之角色。對此種結果,個人深感慶幸與榮耀。
四、 鄉土題材之開發與畫風之建立
鄉情之呼喚 清末民初,白石老人將藝術題材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,以之筆墨娓娓道出真摯之情感、濃郁之鄉情、土壤之芬芳、林野之禪趣……墨韻詩情,無一不令人叫絕,此種回歸鄉土雅意,展現平民生活甘苦,刻繪市井陋巷樸眞之題材,使畫面滿溢盎然生機,使意蘊深涵詩趣哲理。此種鄉土野趣之表現形式,極端平易近人,最為親切自然,個人深深感動,心存嚮往。 於是,一九九一年開始,個人創作方向乃移往本省之鄉間景致與色彩。看農村秋收季節之金黃稻穗,看幼時農家籬前屋後遍植之翠綠蕉園,看阡陌之間常見之油菜花黃,看校園裡公園邊笑靨迎人之鳳凰花紅,山間溪谷搖曳多姿之串串芒花……此雖不若日本北國秋紅之艷麗與嬌美,然樸質中蘊涵豐腴色彩之土親鄉愁,正乃寶島最獨特亦最撩人心緒之風姿與形貌。 尤其,個人以務農之家,年少時代變熟悉荷鋤之辛勞,「晨興理荒穢,帶月荷鋤歸」之深沉記憶,至今猶刻骨銘心,歷歷如昨。於是,透過畫筆,賦予畫面鮮麗之色彩,塑造嶄新之生命,透過墨韻,重溫兒時舊夢,再現往昔記憶,每一創作,莫不意蕩神馳, 心有戚戚然。 其中較可觀者如: 黃色系列之「金穗白垣」寫搖曳逞姿之金黃穗浪。 綠色系列之「歸鄉夢」寫瀟瀟淅淅之翠綠蕉園。 紅色系列之「艷紅」寫紅艷如日燒之鳳凰胭脂。 灰色系列之「那羅印象」寫連綿不斷之台灣山巒。 蜿蜒曲折之山坡梯田、素艷雪凝之梅林景致、古意盎然之農家古厝…皆為年來著筆之主軸,若探就比較此類創作與往昔作品之差異,可以察覺往歳艷麗之色彩,已隨歲月之篩網而日漸淡化,代之而起者,乃素雅淡泊之墨韻情趣與溫馨之氣氛營造。
九二一之憾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,是個不堪回首之日,當天,地牛肆虐故里─南投,山走樓塌,物換人非,佳景遽改,頓時,人們失去了人生之方向,失去了生活之重心,仰天長嘆,亦換不到上蒼之憐憫,此情此景令人戚然。 關懷故里,我畫我鄉,故鄉之斷垣殘壁,舊城深院便逐漸成了我創作之軸。創作之同時,期待早日重建舊家園,恢復舊秩序,拾回昔日安居樂業,樸實無憂之繁榮景象。 |
|
|